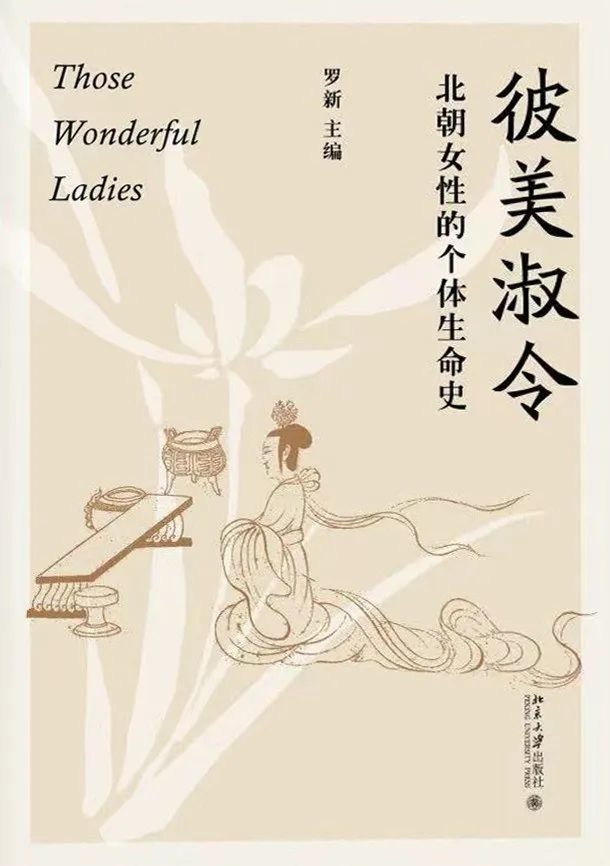
“石头”关联着冰冷,是旧石器时代的弹药,是古人堆砌陵寝的用料,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温度的事物。但当石头承载起文字,自有汉一代开始,以一方墓志的形式安然躺卧在墓穴之中,那些镌刻着个体生命的隐秘叙事,便使其赋予了深沉鲜活的魅力。罗新主编的《彼美淑令: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》,和他先前的作品《漫长的余生: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》一样,通过对深藏于暗黑之下的墓志铭以及部分现有史料的考证,探寻起那些被遗忘、被忽视的微弱生命和历史片段,把湮没在滔滔巨浪中的“细沙”一粒粒捡拾了起来。
重现多元女性
自“历史(history)”一词诞生以来,其男性叙事(his story)的属性就已经注定。且不谈平民女子,就算是出身名门贵胄的女性,也几乎都成了正史忽略的对象,只有以妻女、节妇等依附男性的身份出现时,她们才会破例留下印记。相比而言,墓志铭却有些不同,虽说女性志主的出现频率仍然无法与男性并论,但难能可贵地拥有了自我的叙事。
《彼美淑令》收录的11篇墓志铭解读,其主体正是女性。当我们被裹挟在当下漫无边际的偶像剧、架空剧中,早已理所当然地认为,凡是公主嫔妃没有一个不娇滴任性、凡是皇亲国戚也无一不备受尊崇时,《彼美淑令》则借助于对真实历史的挖掘,向我们展现出了另外一组截然相反的图景。
《陈留公主》里的主人公北魏陈留公主,一生婚姻可谓毫无幸福感可言,先是嫁给北奔入魏的南朝宋文帝之孙刘承绪,虽说也是“公主+王子”的经典“CP”,但对方“少而尫疾(脊骨弯曲)”、体质极弱,明摆着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联姻;羸弱的刘承绪,婚后不久就一命呜呼,陈留公主寡居多年,又改嫁给了同样北上的琅琊王氏后裔王肃,然而,随着王肃在南朝的妻女投奔而来,一场极为狗血的“三角婚姻”又摆在了陈留公主面前,当她把一切都处理妥当,第二任丈夫王肃也不久去世,遭遇二度寡居的陈留公主,此时才三十岁出头,可谓命途多舛。至此,有过两段婚史的陈留公主,似乎已经坐实了“政治婚姻受害者”的人设,不过,随着更多史料和墓志的拼凑,另一个陌生的陈留公主又浮现了出来。贴附在她身上原本“逆来顺受”的标签隐而不见,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女性的独立意识,特别是面对冯太后的逼婚,陈留公主驰马来到皇兄孝文帝的大营,直指冯太后与宫人私通,并自陈誓死不嫁冯夙——如此壮举,就算放置在1500年后的今日,也同样令人称勇。
北宋史学家曾巩在《寄欧阳舍人书》中写道:“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。”相对于史籍的秉笔直书,墓志铭的局限性则体现在趋善避恶上,古往今来的任何一块墓志铭,都很难寻觅到对志主的苛责,也几乎无法触摸到志主的任何不幸。书中的《找回失落于尘土中的故事》一文,以元渠姨的墓志铭为研究对象,三百余字的墓志中,充斥着对元渠姨各种美德的颂扬,在介绍其婚姻时,墓志的撰写者更是浓墨重彩地称赞她与丈夫段韶:“既而作合君子,和如琴瑟,蘋藻成德,绮练增华。”千余年之后,我们虽然已经无法完全洞悉元渠姨婚姻的“幸福指数”,但在北魏末年高氏掌权的时代,元渠姨虽贵为皇亲国戚,其皇室地位早已一落千丈,元渠姨依附于权臣段韶,苟延残喘式的求生状况也可想而知,至少绝非墓志铭描绘的那般简单纯粹、幸福美好。正如罗新在旧作《有所不为的反叛者》一书中所说:“历史越是单一、纯粹、清晰,越是危险,被隐藏、被遗忘、被改写的就越多。”只有当这些鲜活女性的多元性被拼凑出来之时,我们才得以真正触摸她们的体温。
延展历史脉络
史书的叙事重点是历史事件而非历史人物,人物服务于具象化的事件和场景,得到的都是碎片化的呈现;相比而言,墓志铭对个体命运的交代则相对连贯,但笔墨又过多地集中在生世、德行、操守等约定俗成的方面。倘若把两者比照起来,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到更为精彩丰富的人生形态,也有了弥补历史空缺、探究历史真实的另一种可能。
在墓志铭中列举死者的亲族状况,是极为常规的操作,书中收录的《寻找仇妃》一文,从一块稀疏平常的元举墓志,洞察出了极为特殊而珍贵的内容。元举墓志详细介绍了志主四代的宗室情况,不仅填补了《魏书》等现存史料的空白,让我们得以推导出历史人物原本无从考证的生卒年代,同时也隐秘地抛出了一组历史悬念:元举贵为初代宗王的曾祖、祖父,其配偶竟然都是底层官员之女,夫妻身份格外悬殊;而到了世袭王位的父亲和志主,其结姻对象才是高官显贵的女儿。作者以元举曾祖元桢的配偶仇氏为突破口,在对《魏书》《新唐书》等史籍的爬梳剔抉中,让仇氏“罪臣之女”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。仇氏因生父被诛,年幼时便被收入宫掖充当“罪奴”,当时“诸王十五,便赐妻别居”,“然所配者,罪入掖庭”。元举的墓志铭尊称仇氏为“曾祖妃”,但实际上,仇氏只不过是当时被用于赏赐和分配的性资源而已;历史的残酷虽未在墓志铭中得到直接展示,但又恰是墓志铭,让难以掩饰的真相浮现了出来。
《北魏最著名的比丘尼僧芝》是《彼美淑令》中最具考证意味的一篇。太武灭佛后,北魏历代皇帝尊崇佛教几乎众所周知,但囿于时代久远,除了帝后礼佛图等传世石刻以及少数著述外,当年佛教传播的情状很多已不为人知。然而,志主僧芝的墓志铭却贡献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细节,比如,从“(僧芝)诵《涅槃》《法华》《胜鬘》廿余卷”,就可推知,以上三部经典在当时的北魏佛教界已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,这在正史中从未有过著述;再结合僧芝时年居住于关中,而《胜鬘》二十多年前才在南朝都城建康首译,又可推知南北佛学并未因政权分裂而交流阻断。又比如,《僧芝墓志》与另一块《慈庆墓志》是北魏唯二两处提到“比丘尼统”这一宗教首领职务的历史记录,倘若如此两块墓志还长埋于地下,我们可能永远只会知道有针对男性僧人的“沙门统”,却不知也有管理女性僧人的“比丘尼统”,“沉默的石头”以微小却不可忽视的作用,一点一点地填充着历史的巨大沟壑。
挖掘个体真相
文学评论家勒内·韦勒克曾经说过:“个体发生史重现种族发生史。”仍以《寻找仇妃》中的仇氏为例,无论史籍还是墓志,对于和仇氏一样的“罪奴”的遭遇,都只是简简单单地描述为“家难”或是“遭家不造”,但潜藏于只言片语背后的却是“全家成年男性被诛、成年与未成年女性入宫为奴的惨痛家史”;同样,在《找回失落于尘土中的故事》一文中,《北史》对元渠姨经历的陈述虽然也只是“匿娄太后家,终文宣世不敢出”这看似平淡的12个字,但在如此轻描淡写的命运书写中,却涌动着北魏末年整个元氏家族风雨飘摇的暗流,北齐文宣帝高洋亲自策划的那场惊天骇地的“天保屠杀”也正席卷而来。
“所有历史都是成王败寇史”,收录在《彼美淑令》中的《常山公主事迹杂缀》,正是以宣武帝登基后,孝文帝之弟元禧遭遇杀戮的故事,铺陈着这样的残酷逻辑。在官修的《魏书》中,元禧被塑造成了“潜受贿赂,阴为威惠”“性骄奢,贪淫财色”的糟糕形象,而在《魏书》之外又几乎没有元禧的任何记录,《常山公主事迹杂缀》细致梳理了常山公主、宁陵公主、李媛华等与元禧密切相关的墓志,但它们对元禧生平事迹的涉及,要么是空白,要么也只有名字。个体叙事已然噤若寒蝉,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正史,之所以在排他的语境下痛下刀笔,无非就是为了证明元禧之死罪有应得,然后,堙灭在这种“罪有应得”之下的,可能就是一个永远都不为人知的真实生命。史书还记载,元禧死后,“诸子乏衣食”,就如同复刻了同时代的陆安保,在与兄弟陆昕争夺袭爵之后“沉废贫贱,不免饥寒”,个体生命的荣辱兴衰,竟在风卷云残的时代洪流中时沉时浮、无所归依。作为对正史的对照,墓志铭这种极具私人化的记事,在宏大叙事之外,让那些独特而丰富的小我生命,在另外的维度铺陈开来,绽放出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独特光彩。
作者|易扬 编辑|罗皓菱
